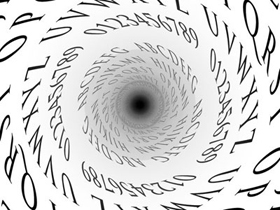「音節分析」與中文閱讀困難的關係及對教導有關學童的啟示
引言
七十年代初,西方學者如Rozin, Poritsky & Sotsky (1971)曾表示英語系統內的學童閱讀困難情況較中文系統內的為嚴重,原因是英語是拼音文字,讀者須掌握「形聲配合」的規律﹙symbol-sound correspondences﹚才能幫助閱讀能力的發展,要懂得「形聲配合」的規律,學童便要懂得字內音詳分析,惟英語的「形聲配合」是頗為複雜及抽象的,如DA在DAD, DATE, DAM的讀音都有所不同,學童在領悟其中形聲關係有困難時,便容易發生閱讀障礙。
而Rozin等人認為中文字都是圖畫,可從字形中直達字義,因不用分析字音,便減少了閱讀時會遇到的困難。他更嘗試用中文字代替英文字來教導一些有閱讀障礙的美國兒童,發覺他們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更認定中文字易於學習,閱讀困難並不存在中國人的社會中。
當然,Rozin等人的研究存在不少問題,如學生們會否因事物新奇而加倍用功,又如選取的教學內容是否適當等,都未有適當的控制,但無論如何,Rozin等人的研究卻刺激起中文閱讀研究者的興趣。 Stevenson, Stigler, Lucker, Lee, Hsu, & Kitamura (1982)曾研究美國、日本、台灣三地的閱讀學習的情況。而第375及377期的香港教協報,亦有提及香港讀寫困難的情況,雖然真正有閱讀困難的學童的數字並不知曉,但教育署及醫務署每年都驗出百多個案,證明閱讀困難在中國人社會亦十分普遍。現在希望探討的,是引起中文閱讀困難的成因及教導該類學童的方法。
西方拼音文字方面閱讀過程及閱讀困難
在西方拼音文字中,Frith (1985)認為閱讀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Logographic Stage,主要是認字的外形,如頭或尾的字母;第二個階段是Alphabetic Stage,學童在這一個階段開始認識及運用拼音的技巧。而第三個階段則是Orthographic Stage,會據字的外形能準確讀出整個字的讀音,及能串出該字而不用經過拼音的過程。每一個階段的發展均建立在另一個階段之上。
而Coltheart (1978)及 Morton & Patterson (1980)等人亦認為閱讀時,並不單止限於一種途徑,即必要經「形聲配合」。因一些字彙如 have, island等亦不限於「形聲配合」的規律,閱讀這些字彙時,必須經從另一種途徑。Coltheart (1978)提出「雙途徑閱讀模式」(dual-route model of reading),認為閱讀的途徑有二種:其一是「聲的途徑」(sub-lexical procedure),在閱讀時,會先分析字內的音節才至字義;而另一途徑是「義的途徑」(lexical procedure),即從接觸字形開始,即可知道字義。一個熟練讀者,會同時利用兩種途徑進行閱讀。通常遇上一般熟識字彙,會利用第一種途徑,而對一些艱深字彙,則會用第二種途徑。
「深層閱讀困難」和「表層閱讀困難」讀者的特徵
Coltheart等人又從腦受損的讀者中,發現一些人會忘記讀某一類字彙,卻會讀出另一類字彙。例如一些讀者能讀出「不規則字」(irregular words),例如pint, colonel等字,所謂「不規則字」,即他們並不根據「形聲配合」的規律的,學會閱讀這類字彙的途徑,惟有靠認識整個字而不用分析字的音節,而這些讀者卻不懂得閱讀一些「假字」(psuedowords),如bemp等,而假字是跟從「形聲配合」的規律的,這些字不是真字,是沒有意義的。由此推斷,這一類讀者能運用「義的途徑」(lexical procedure)進行閱讀,卻未有效地利用「聲的途徑」(sub-lexical procedure),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他們的「聲的途徑」受損或阻礙,Coltheart稱這一類讀者有「深層閱讀困難」(deep dyslexia)。另一些讀者的情況剛好相反,他們會讀「假字」,卻不懂得閱讀「不規則字」,Coltheart稱這一類讀者有「表層閱讀困難」(surface dyslexia)。一般來說,在拼音文字當中,如未懂得分析字中音節所遇困難會較其他因素為大。
中文方面閱讀過程及閱讀困難
中文的閱讀過程
至於中文閱讀方面,情況是否如西方拼音文字一樣,要懂得分析字內所包含音節,才可以成為一個熟練的讀者,相信還需要深入分析。五十年前,艾偉 (1948)已表示漢字的形、音、義三部分有密切的關係。稱「所謂識字謂見形而知聲、義,聞聲而知義、形也。故以形為刺激須引起聲、義之反應,以聲為刺激須能引起形、義之反應。」艾偉雖然指出閱讀漢字的過程中,形、音、義互相有影響,卻仍未有仔細指出三者在閱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不少人都認為中文是表達文字,閱讀中文字時,可從形直接知道字義,因中文字的部首都含有一定意義,讀者可透過首部包含的意義而了解整個字的意義。雖然據現時的估計,形聲字雖佔約有百分之八十,但可從聲旁而推測整個字的讀音卻不足百之四十,約只有百分之三十八對讀者有幫助。當然,亦有不同的意見存在,Tan & Perfetti (1997)認為無論中西方文化在閱讀過程中,必經「形聲配合」的過程,如閱讀「表」字時,讀音只有一個,但解釋則可與「表面」、「表達」、「表現」等作聯繫,由此可知,形與音的關係很直接,並有決定性,而形義的關係則較複雜,須經多重考慮才能決定其中是那一個關係,Tan & Perfetti因此提出「決定原則」(Determinacy Principle),認為形聲關係或形義關係中,那一種關係先行,是決定於誰先作啟動,上述例子,肯定形音會先於形義的。
閱讀困難的現象
而尹文剛(1990) 在其腦受損的中國讀者中,亦發現與Coltheart所提及的閱讀困難的現象存在,尹文剛的部份讀者在閱讀「規則字」及「不規則字」時,明顯地「不規則字」的錯誤多於「規則字」,如「埋」讀作「里」,又「秤」讀作「平」等。同時,亦有部份讀者會讀出與所要讀的字的同義或近義字,如「貓」讀作「狗」,「泥」讀作「土」等。Elliott &Ho(1996)亦曾在有閱讀困難的學生中,找出其中部分的學生存在「表層閱讀困難」及「深層閱讀困難」的徵狀。其中部分學生閱讀「不規則字」時的表現比「假字」時為好,而部分學生的表現卻剛好相反。
由此證明,中文字閱讀亦可經從「聲的途徑」或「義的途徑」進行,一般讀者會視乎所閱讀文字的深淺及常見的程度等,才決定運用那一種途徑進行閱讀。同時,亦證明Coltheart所提的「表層閱讀困難」及「深層閱讀困難」在在中文的讀者上。至於「聲的途徑」的損害是否中文閱讀困難的主要原因,仍要作深入研究才能下定論。
無論如何,現實的情況是一些學童只能運用「義的途徑」或「聲的途徑」中的一種途徑進行閱讀,因此便引起不同的閱讀困難。只能用「義的途徑」的話,他們閱讀「不規定字」時表示會較讀「假字」為佳,又?把同義或近義的字混淆,如「犬」讀作「狗」,「日」作「月」等,同時,他們學習有實質意義的字彙時,會較抽象的字彙為容易,名詞及形容詞的學習較連接詞副詞等為容易。至於只能運用「聲的途徑」來進行閱讀的學童,他們容易把「同聲字」混淆,閱讀「不規則字」的表現不及「規則字」,惟他們會讀出「假字」。
教學方法
在教導有閱讀困難的學童時,應根據他們的弱點進行針對性教導。在五十年代末,遼寧省北關小學提出的「集中識字法」中的「基本字帶字」的方法應可作參考。以「基本字帶字」,利於形成認知結構,培養學生獨立識字的能力。如能充分利用和發掘漢字本身在音、形、義方面的信息,便會方便各類閱讀困難的學童學習,減輕他們的識字記憶負擔。
針對「深層閱讀困難」的學童
對「深層閱讀困難」的學童來說,他們的障礙在於「聲的途徑」(sub-lexical procedure)有阻塞,多會利用「義的途徑」(Lexical Procedure)來閱讀。在教導他們時,便應針對他們的弱點,利用「集中識字法」,把一系列同音或近音字,如「清」、「靖」、「清」等列出,讓學生留意各字的讀音,領悟其中共通的地方,跟著指出共通點是以表字發聲為主,其後,又可加入其他有共同特性的字彙,如「菁」、「晴」等。而最後是列出一組「青」字旁為主的字彙,使學生指出那一些與「青」字同音或近似的,而那一些又不是。
針對「表層閱讀困難」的學童
同樣地,對「表層閱讀困難」的學童來說,他們的弱點是未能善用「義的途徑」來閱讀,因此,教導他們時可把同義或近義集中一起,動物類的字彙如「貓」、「狗」、「犬」、「羊」便可等集中教導。當然,同部首的字彙,如「河」、「洋」、「流」、「海」等亦可集中教導,這些字彙都是與水有關的。
因此可見,教導閱讀困難的學童,可就漢字的特性,利用聲旁或部首來教導不同類型的閱讀困難學生。在對症下藥的方法教導之下,希望可改善學生的識字能力。
「多種感官教學方法」(Multisensory Method)
同時,對一些學習困難較嚴重的學童來說,在未利用漢字部首或聲旁來教導前,可試用「多種感官教學方法」(Multisensory Method),讓他們先對字的結構作了解,才運作「集中識字法」使他們認識更多字彙。
一般「多種感官教學方法」是利用觸摸、模仿、記憶等刺激學生從不同渠道認識字形結構,從而幫助他們學會整個生字,這種方法,曾證實對一些有嚴重閱讀困難學生十分有效。這個方法以個別教學為主,主要有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先要徵得學生的意願,願意作出努力,因過程頗為繁複,學生要集中精神,付出才會成功。正式學習時,首先是選取一個生字來學習,生字的筆畫或深淺不用理會,主要使學生知道該字的意義;跟著是寫出該字,在寫字時,教師坐在學生邊旁,務使學生看著和聽著教師的動作及說話,其中的過程如下:
-
教師說出該字;
-
用粗筆把字寫在一張4吋乘11咐咭紙之上,一面寫字,一面讀出該字的筆劃;
-
用手指臨摹該字;
-
接著是讓學生模仿書寫該字,在這一個階段,不用對學生解釋任何程序,只要學生留心教師的說並跟著:
- 說出該字
- 用手指摹仿寫字。讓學生把手指放在紙上,一面寫,一面跟著教師讀出該字的筆劃。目的使學生了解整個字的字形及最後讀出該字的讀音
- 重複上述過程
-
學生繼續練習,至認為不用在粗筆字模仿為止;
-
跟著是自行寫出該字,在書寫時,仍須留意筆劃的暢順,如學生在書寫途中有錯誤時,著學生重寫一次;
-
如學生重複書寫而沒1有錯誤時,便可讓學生學習新的字彙,這一段學習時間的長短並沒有限制,務求學生學會指定的生字為止;
-
把所學的字紀錄下來。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學生經過模仿的階段後,把所教的生字的每一筆劃一面寫一面讀出,讓學生跟著每一筆劃讀,教師跟著把字蓋上,使學生憑記憶寫出該字。
第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與第二階段相同,但不再在學生面前逐一筆劃寫,只出示整個字。教師把生字讀出,學生跟著讀及憑記憶中寫出該字。
第四個階段
第四階段是把所學會的字彙仿聯繫,跟著同部首或同聲字歸類,一如「集中識字法」,以「基本字帶字」,增加學生的字彙,從而改善他們的閱讀能力。
總結
其實,閱讀困難的原因有多種,在西方拼音文字中,則以未懂得「字聲配合」規律為主要原因;對中文來說,這亦是一個閱讀困難的成因,但是不是一個最主要的原因,還要作深入研究。無論如何,在教導有閱讀困難的學生時,可運用中文字的部首及聲旁的特性,針對不同類型的閱讀困難學生仿教導。當然,除形聲配合外,感知、肌能、記憶能力、興趣、動機、外在環境刺激等因素對閱讀能力發展都可能有影響。因此,教師在教導有學習困難的學生時,應仔細觀察,分析困難所在,從而改善學生的弱點,提高他們的閱讀能力。
參考文獻
尹文剛 (1991)。《漢字失讀的類型與意義》。心理學報。十二期。頁297-305。
艾偉 (1948)。《閱讀心理、漢字問題》。中華書局。
Coltheart, M. (1978). Writing systems and reading disorders. In G. Underwood (Ed.), Strategi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London: Academic Press.
Elliott, R. & Ho, F. C. (1996). Sub-types of Dyslexia in Chinese Writing Syste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96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AARE) and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ingapore (ERA).
Frith, U. (1985). Beneath the surface of the developmental dyslexia. In K. E. Patterson, J. C. Marshall & M. Coltheart (Eds.), Surface Dyslexia: Neuropsychologic and Cognitive Studies of Phonologic Reading. Hillsdale, NJ: Erlbaum.
Morton, J. & Patterson, K. (1980). A new attempt at an interpretation, or, an attempt at a new interpretation. In M. Coltheart, K. Patterson & J. C. Marshall (Eds.), Deep D Dyslexia.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Rozin, P., Poritsky, S. & Sotsky, R. (1971). American children with reading problems can easily learn to read English represent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Science, 171, 1264-1267.
Stevenson, H. W., Stigler, J. W., Lucker, G. W., Lee, S. Y., Hsu., C. C & Kitamura, C. (1982). Reading disabilities: the case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English. Child Development, 53, 1164-1181.
Tan, L. H. & Perfetti, C. A. (1997). Phonological codes as early sources of constraint in Chinese word identification: A review of current discoveries and theoretical accounts. In C. K. Leong & K. Tamaoka (Ed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Languag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作者簡介
何福全博士為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Robert Elliott is th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本文為轉載自《香港特殊教育論壇》(1999年第二期第二號)